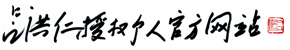“无情岁月增中减”,转瞬间已到八十余岁。唐人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朱自清先生却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值此百年未遇的盛世,确实无须惆怅。但就小我来说,来日无多,岂不可惜。年迈之人多喜欢忆旧,这也可能是一条规律。许多亲朋好友,许多老同学、老同事天各一方,有的已经仙逝,有的很少通讯,更难作长谈,为此想整理一些旧作,编个小册子遥寄各方,聊作一席谈。于是就此开始了这本册子的编撰。
我的一生几乎都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小学时期正逢抗日战争爆发,在清波中学学习阶段是在沦陷时期度过的,从就读湘湖师范到考进国立艺专读书,正值国内战争、共产党赶走蒋介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却先天不足,虽然我是绘画系毕业,但学习时间除掉历史变动过程时期和解放以后的各项运动,斩头去尾,实际上所谓五年制,确切学习时间最多不过三年有余。不像现在的学生,附中四年、大学五年、研究生三年、出国两年那样的幸运。有些青年教员或出国留学,或进专家训练班,最起码也到北京去进修或是本系毕业。但就比起另外许多人来说却又比他们有较优的条件,因为在我执教期间,全院教职员工四百余人,与学生的比例是1比1,每年招生一个班只有8到12人,所以在教学指导之余可以与学生一起画习作。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也可以起点示范作用。也有轮流进修的机会。学院有时又组织教员去大型展览会中临摹。为此我想谈谈我是怎么对绘画产生兴趣,又是怎么又学又教和怎样经受折腾的。
我对绘画产生兴趣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初小时我在嵊州市(原嵊县)城里二戴中心小学上学,当时我二嫂的外婆家在城里开一个文具店,兼营连环画出租,为此我就有机会在那里饱览各种连环画,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火烧红莲寺》、《恶僧果报录》,影响了我的性格塑造,也使我对绘画产生了兴趣。我很佩服能画这种画的人,上海连环画家赵宏本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于是我也经常在小学生用的“石版”上用石笔畅意涂抹,表现连环画中英雄人物的气势动态。
九岁那年我父亲积劳成疾病逝,母亲带我们全家迁回老家嵊西楼下村,我也就转到上沙地继锦小学读书。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响,广泛流传的“平型关大捷”连环画很鼓舞人心,我二哥又寄给我许多16开本的《老百姓》杂志,其中有俞乃大先生画的抗战小故事,如《诸暨人民杀敌记》等等。而继锦小学的一些青年教师如佘惠民、吕侠南先生都很进步,组织演出抗日话剧《麒麟寨》,就叫我去画海报。许多年后才知上沙地当时已有我们的地下党在活动。由于如此等等的影响,在小学时我就自编自画抗日小故事发表在学校墙报上,得到校长的表扬。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清波中学里度过的,清波中学原来的校址是在杭州,因为当时清波中学的校长裘颂兰先生是嵊州西乡白竹人,为避日寇,迁校到嵊州,校址就在新沃的祠堂里。我家离新沃五华里,每日要自带中餐走五里路去上学,其时我大哥已参加金华军医训练班,六个月后就开赴福建前线抗日。二哥在因避难来嵊州太平镇的宁波中学公费求学,不久又因日寇紧逼而向东阳、缙云等山区内迁,但他还是经常捎给我一些抗战画报,其中有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也有两个“大和武士”比赛杀人的照片,还寄给我不少《子恺漫画》;学校的美术老师虽也教我们画点静物,而擅长的却是给我们讲故事,所以我就临丰子恺先生漫画过瘾。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不久日寇就进入嵊州,由嵊长公路直扑金华。沿途飞机前导,大炮向可疑目标轰击,十分耀武扬威。而我家所在地正是日军右翼经过的小村,我的一个族叔因逃避不及,被日寇抓去,跪在地上被刀架在脖子上,吓得半死。近村也有数人被日寇枪杀。嵊州沦陷后,鬼子就在公路沿线的大镇甘霖、长乐等地修筑碉堡作为据点,随心所欲地四处骚扰。有一次日寇来袭击乡公所,理由是乡长抗粮。乡公所离我们学校仅二三华里,是设在大仁寺内的。寺左是小山,日寇抢占制高点后即向目标扫射,幸而乡公所及时得到情报,人员迅速撤离,只死了一个伙计。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就提前放学,学生刚走出祠堂大门,走到门前晒场上,鬼子机枪就向我们扫来,于是我等就朝反方向狂奔,好在这次只伤了一个同学叫周海虹,子弹从背部肩胛骨上进去从前面锁骨下穿出。而在田里作业的老百姓被打死七八个,大仁寺也被焚毁。又一次鬼子经过我们村时,我母亲知道后立即狂奔,并急中生智,迅速跳入池塘,躲在沿边草丛下,幸免于难,但村里有些躲在树林中的妇女却惨遭强暴。国仇家恨,从小我就铭刻在心,直到现在我还十分喜欢看那些抗日的故事片。
在沦陷后期,嵊州曾有一次联乡队围剿伪军王保部队的联合行动。事后由我哥哥编写连环画剧本,由我创作,约画了七八十幅,分两册装订,可惜后来借给了人就无下落了。
中学毕业后,我曾去南山毫岭的保国民学校教过书。年俸六百斤稻谷,只够吃饭,饭自己烧,学生的家长有时自动送点咸菜毛笋来。我在课余时间自画自刻了一本漫画集,由另外两个好友具名,完全是学丰子恺先生的画法,自印三十余本,幸好现在还保留一本。由于地处偏僻,我几乎与外面极少有联系,所以连日寇投降的消息也不知道。
1946年郑峰同志来约我去报考湘湖师范学校,两人都考取了。到了湘师,在图画教室里见到了石膏像,才知学画可以从写生入手。
艺专从四川搬回杭州外西湖孤山原址后,二哥鼓励我去试考,我考上了,就这样从1947年下半年起进入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五年制预科。
1947年来杭考试时,我住在南星桥火车站边一个远房亲戚家,他们住两间茅屋,摆一个烟酒杂货和花生瓜子的小摊谋生。但当我见到住地附近拉板车的工人,回家时能带点小菜和鱼时,感到大城市确比农村好,在农村里像我家这样“鸡顿鼓”人家(意即能吃饱饭的),吃鱼得等到过年的时候,而且是从塘里车干水后自行捉来的。当时我也不了解城里的工人,一日不干就得饿肚子。我的族叔,在杭州沦陷时,日本鬼子来抢他家养的猪,他只是去拦了一拦,就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
进艺专我读的是五年制,头二年学基础叫预科,预科后才能进入本科,本科分国画、油画、雕塑和图案,可由学生自选。当时油画有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倪贻德等教室(相当于现在说的工作室制)。我们一开始是吕霞光先生教素描,他去法国后由周圭、周碧初先生执教。我也学国画,是潘天寿先生的得意门生高冠华先生教的,教临摹,也有其他文化课和美术史等。素描画石膏头像,不画几何模型,用木炭和木炭画纸,这种纸是进口的,很贵,一般穷学生只能画了擦掉再画,或则用肥皂板刷擦洗了再画。素描课是教师个别指导,几乎没有讲什么课。市面上技法理论书也很少,几家旧书店里也只有黄觉寺先生编的《素描述要》和倪贻德先生的《水彩画法》等。平时课余就由学生自行外出写生。我主要是画水彩。当时我们班上娄世棠的素描和潘其鎏的水彩画得最好。
到1948年国内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校内外斗争也十分尖锐,“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于子三事件”、艺专五同学被捕……连学校招生都成为斗争的场地,会有进步同学和反动当局组织的两个招生委员会来拉考生介绍学校当时的斗争情况。不到二年级读完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的5月杭州就解放了。我们许多学生都自觉地跑到断桥去迎接解放军。解放后的第二天,解放军即刻派代表来学校看望学生。我们四七级原有学生35名左右,到解放时,大部分参军去了,小部分自行星散不再来校,也有些跟校长汪日章逃走,欲去台湾,在宁波被解放军截住,在校只剩下9人,到1950年才招生补足一个班。1950年军管不久,南下干部就接管了学校:推行新文艺方针,反对形式主义,提倡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增加创作课,下乡下厂向工农兵学习。目标明确,气象一新。1952年冬全院到皖北参加土改四个月。此后政治运动不断。其时文人画也在批判之列,著名画家诸乐三先生被弄到财务科去执掌算盘,国画改成彩墨画,并从学生中抽调一批写实基础好的去搞彩墨,“浙派人物画”也由此起势而渐成气候。那时在校的青年学生在党的思想教育下虽然生活清苦,但深感解放军英勇善战,共产党的干部廉洁奉公,国家前途大有希望,所以都愿意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时大家表态服从党的挑选,有的像周昌米那样投笔从军。到毕业分配时我们所填志愿,都是愿意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我们将毕业那几年(1952年前),在素描课上,强调线描为主,由庞教务长主持将学生成绩作阶段性的评奖,得奖者发五角星一个,中间又可嵌入小五角星数枚,得一次奖,嵌入小五角星一颗。我还得过好几颗(五角星奖章还在)。从我们毕业前到此后的多年,强调以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主,并紧密联系社会。所以当时上海、北京及浙江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常派人来校找师生组稿,我们合作的连环画《祝福》也是在1956年画的,后来还出过精装英文版。我还单独画过《大冬瓜》,被译成朝鲜文出版。我们的毕业创作是彦涵、张怀江先生指导的,关良先生教我们油画。
当时教学思想上也不统一,政治挂帅,为工农兵服务及后来向苏联一边倒是艺术界开展的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搞创作,突出主题思想,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为了争取革命胜利,在一定条件下强调一下某种需要,是无可非议的,历来如此。我们的老祖宗也主张文艺有“助人伦,成教化”的功能。
遗憾的是“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在工作生活中层层加码,把熟悉生活强调到“浙江人要画浙江”,以至于创作题材撞车,表现形式千人一面,到文化大革命时更走上毁灭传统、毁灭文艺的绝路,并闹出离奇的笑话。例如油画系的红卫兵小将,扬言要超过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结果画了张很大的油画,画中去掉了刘少奇,把毛主席向游行群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去掉换成林彪在挥手(此画和我有缘,因参与绘制的小将们画不好画中二排站着的周总理形象,命我去改好,所以我见到过此画)。可是没多久林彪自我爆炸了。发展成这样的艺术密切配合政治,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括子。
我毕业后的第二年(1953年)就被派到大学部去教速写,这是一门根据创作需要而新开设的课程,学生是新从育才学校併过来的小青年(郑圣天、刘文西班)我也没有画过多少速写,王流秋先生给了我一个简要的提纲,我就赤膊上阵了。那时我住在苏白公祠(即现在太和园的旧址)。我就只有一边上课一边拼命找资料。记住叶浅予先生谈速写的要点,每周九节。其实我觉得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在速写课上,因为速写是要以素描为基础的,主要是用简练扼要的手法,抓住对象稍纵即逝的神气。速写要画得好,当然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需有文化修养等内涵,后者非朝夕可得,开课只能是应急,如学生能平时抓紧课余练习,同样可以解决问题。但这样一逼也逼出了我和吴德隆于1958年合写出版了一本《怎样画速写》。这本小册子除一般手法外,强调了目识、默记,没有多少心得体会,但却行销了十五年。
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艺术教学与科技教育不同,艺术教育带有一种强烈的个性,教员都是根据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去指导学生,由于个人的艺术道路的不同,也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教学方法。强行用某个人的观点去统一衡量某一种表现也是有害的。”由此也可以演绎为各人可能或可以有各人的爱好。在我的实践、教学与学习中,我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在我接触到的一些老一辈留法教师中,除了颜文 院长外,在素描和油画教学上,都没有谈出多少观点与方法来,多是就画论画地指出此地要稍画高一点,此地太黑,要眯起眼睛来看等等,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已使他们“噤若寒蝉”,还是因为虽然自己画得好,但画得好不一定就教得好的原故,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当时不教素描的黄觉寺先生写过一本《素描述要》,却比他们要讲得更多一些。因为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国画的理论,也听过潘天寿院长的“中国画史讲座”,所以印象很深,对国画中的“六法论”和作画要从“有法到无法,有法之极归于无法,无法之法乃是至法”等论点,深有同感。而在我们毕业以后的几年中,理论教研室大力翻译了“契斯卡阔夫教学法”和“苏联教学大纲”,学校也大力组织学习、讨论。绘画系的宋秉恒先生与丁正献先生等结合他们自己的经验热烈探讨方法步骤。我们这些年轻的留校教员,都参加听课并详细笔记。我觉得运用契斯卡阔夫的一套,再加上形象教学(即有分量的示范作品)的辅助,可以很快地提高自己和教好学生。例如许多人都说画好素描要学会“整体观察”。指导学生素描时也经常发现有的学生不会整体观察,我就学习颜院长谈心得体会的形式,并结合自己学习契斯卡阔夫方法的心得,把整体观察法的精粹更具体化:即关键在于从相互比较中来确定比例、明暗等诸关系。强调要准确地比较,即必须注意彼此的相关点,并要拉大距离来比较,不能光与相邻的作比较,要把整个对象加上环境,都放在整体之内。为什么要眯起眼睛来看对象?这与盯住一点看有什么差别等等,叫学生自行比较,这样学生就很容易理解。又如:契斯卡阔夫谈的作画步骤,是环环相扣的,前一步为下一步作好了准备,分得过细就繁琐,不前后照顾就会造成返工等等,这也是我自己晚上加码画石膏的实践经验。我后来写的《素描述要》就是我自己的教学经验的总结。此书还被一些培训班作为教材。
写技法理论等工具书,也要像颜院长的《色彩琐谈》那样谈心得体会,这样才能成为开发智慧的钥匙。我学油画掌握色彩关系,也是从看了颜院长在法国写生的纸版油画开始的,那时对他真是五体投地。我曾跟着颜院长去看他画西泠桥。在1957年,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来杭开画展时,我跟着马克西莫夫到卖鱼桥去看他写生:那是一个晴天,阳光照着对岸有排门的店面房子,部分房子处在阴影之中。我觉得他画的颜色比我看出去的对象鲜艳得多,就问他:“怎么我看不出这样的色彩来?是加强的吗?”他说:“我看去就是这样。”当时听了很纳闷!后来想起颜院长谈起过:“色彩是要靠捉的”,“不能盯着看”,才渐渐体会到不是马克西莫夫的眼睛生得特别,而是写生时的观察方法比我们得体而已。写生和素描一样要用“整体观察”。当然要画好色彩,还得懂得色彩三要素,懂得色彩的调和甚至调色板的排列与用色的厚薄等等诸多因素。我们毕业时是绘画系,没有画过几张课堂作业,画出的色彩就像用颜色在画素描(目前许多画册上还有不少人没有突破这一点,除那些有意试探用简单的颜料者外)。结果画面上不是“画粉”就是“酱油汤”,或是不协调的一些色彩的堆积。记得自那段时期起,教员学生普遍学习颜院长和费以复先生的办法采用小油画箱(十六开本大小)用小纸板,可随时随地站着作写生画,我的部分小油画速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现在也还保留部分。纸板虽简单但不裂,色彩也没有多少变色。
在美术教学中,我不赞成过分强调天才。我认为只要此人热爱绘画,认真探求,在较好的教员指导下,可以成为较好的美术工作者,如果教师过分强调“天才教学”,不是不负责任,就是怕在教学上花时间而延误了自已的创作。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印象派的画册图书馆是不外借的,教员只能在图书室内看,学生是不许看的,因为它也是批判对象。记得很清楚有个留法教授也违心地批判印象派是“表现肉体的微微地抖动”,所以是不可取的。只有金冶先生敢在《新美术》杂志上发表文章与批判印象派的领导唱对台戏。
学校也曾派关良先生出访罗马尼亚,并请罗马尼亚专家来办训练班,但据我看都是表面文章,领导上曾经叫我晚上去训练班里讲速写就是证明。而潘天寿先生倒认为博巴的画才是油画。再就是除留苏以外的海归派,也多是名义上的教员,没有安排他们上过多少课。所以说是苏派一统天下一点不假。但从我的切身体验来看,我觉得苏派在基础训练上是给我们打下坚实的基础的。何以见得?其实客观一点看,苏联也是欧洲画派的一支,在油画史上有它的地位与成名的画家。当时苏联提倡现实主义,但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单一化。而印象派以后,国外流派已千变万化。(解放前的国立艺专,也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一套),所以他们的基础练习上早已不是用写实造型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一统天下是政策使然,又不是某个人的罪过。就这点来说,全山石在巩固这套基础的功夫上,是有贡献的。他们带回的作品和临摹作品,使师生大开眼界。但改革开放后,美术界忽然有人责怪契斯卡阔夫来,指责这种方法和明暗五调子是要引导学生入死胡同。在这些问题上,社会上也有“翻烧饼”的口水战,真有些像当年中苏交恶时的情形:连马克西莫夫也因有过来华办训练班事而降了一级之说法。
我认为“画死不画死”,不是使用什么工具的问题,也不是契斯卡阔夫的方法不对,“变与不变”和“想不想变”等问题都是思想观点上的问题。现在这问题已经很清楚。或许当时的口水战是知识分子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不可明言的指桑骂槐,特别是八十年代前后。其时全山石去新疆写生去了,也曾邀我同去,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去,所以系里的会议由我代为主持。这些会议真热闹!因为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措施大快人心,参加会议的人什么想法都释放出来了。当时对这些发泄有些我有同感,有些我不同意,并认为这些是“物极必反”的结果。会上有人说:“这种谈论不要汇报,断章取义的汇报更不好。”但我以为只要没有害人之心,比较客观地反映存在的问题,是我党的一贯做法,所以我只汇报有这些反映但不提是谁说的,却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其实1979年底在我院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艺术高等院校素描教学座谈会”已经比较全面论述了有关方面的各个问题:例如钱绍武先生的发言很有趣“……不管法、德、美、苏,根本内容都是一回事,虽然有芝麻多少、手法轻重之别,而却以面粉为主……” “这种训练方法,要求学生逐渐掌握一套表现方法,逐渐形成带有个性特点的描绘技巧。此点苏德是有区别的,苏强调基本方法的掌握,不强调个性和风格,也不强调艺术处理,艺术韵味等,认为那是美术学院外的事。德法则不同,强调学生某方面的个性特点,很早就加以引导和鼓励,我以为很可贵。”(以上是大意,是根据我摘的笔记),又如对“各种专业是否要有各自的专业素描”、“高低年级是否应该有所不同”,也有的说“过早谈风格……会使学生基础不扎实”等问题都谈到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争鸣好。争持不下,也不要紧,都可以尝试,多年以后,实践会出沉浮,于美术教学有益。
在此期间的教学中,我们已在进行探索。记得上述座谈会召开期间,正值我带油画系潘一杭、林琳班从舟山深入生活回来,回校后就进行了一次汇报展出。因为在舟山时,有不少学生用夸张的手法或印象派的方法画了不少油画速写,我当时发现有的学生,特别是色彩较差的学生进步很快,所以也觉得放开大胆地画有好处。回校后,有的学生却不敢拿出来展览,我就说:“不要怕评论,评论好是你们的,吃批评我负责。”当时包括外校来的教师,反映都不错。
至于我同林琳的争吵问题,我以为主要不在专业上,因为林琳的素描和查粒的用线为主画结构的素描,都是五分成绩并留系作为优秀作品的,好像蔡亮先生编过一本书的封面就是林琳的一张半身素描像,就是我教时留下来的。但我觉得林琳当时较自由散漫,比较放任自傲。舟山回来上船时把调色板甩入大海,行李叫潘一杭挑,我说让他自己背,吃点苦有好处,当然我没有好好做思想工作。后来我就调到附中,他还写信来道歉,我说都有错,改了就好。对他的处理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人来同我说起过此类事。但据说林琳出国后死于非命,真可惜。
对绘画的观点,我很喜欢黄宾虹老先生的说法(王伯敏先生编的《黄宾虹先生画语录》):“画有三:1、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2、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鱼目混珠,亦欺世盗名之画。3、唯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
他还曾说“欲取古人之长,皆为已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确是形成个人风格的写照,当然此非朝夕可就,完成个人风格许多功夫却在“画外”。
“文革”前我好像做过教研组长,“文革”时我曾暗自统计过,当时油画系教职工三十几人,而进牛棚占了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我十分惊奇怎么反革命越来越多了,胡善馀先生是自己要进去的。因为他的出身是贫农,本来不会轮到,但他说:“我还是跟他们在一起好。”“文革”中我是逍遥派,开始我和郑圣天被当成黑支部的左右手,被陪斗了五小时,我是可以在弯腰时用双手撑着膝盖的。王德威先生是走资派双手必须悬空,记得那天我对批斗内容什么都没有听见,只想着如何坚持着弯到最后。王先生精神比我好,我开完批斗会时直起腰来差一点跌倒。油画系有些年轻教员和学生贴大字报要我赶快表态,端正立场,我也不理。有一天陪一个老同学,去游玩了一圈,晚上回来时我爱人说,红卫兵来叫过你,我说不管他,有事他会再来的,睡觉。第二天早晨到饭厅去,看到郑圣天已剃成阴阳头,真像开玩笑。我当时觉得有的人怎么写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很奇怪,问过吴德隆同志,他说这还不容易,这里抄一段,那里摘一点不就一张。又扯远了。
1982年调我去附中主持复校工作。领导找我谈话时,我自知没有治校能力,做个教员或教研组长可以,但院领导说:“这是院党委一致决定的。”我是服从组织决定去的,但还有人说我想做官。这是完全与我为人相违背的。我这人历来不走上层路线,也不会见风使舵,最瞧不起迎逢吹拍,也从来不向领导提过个人要求,评职称,我女儿考学校都耻于求人。
到附中后只有一捆素描和桌椅板凳,也不得不接触许多方方面面。才知道领导上对怎么办附中和要不要培养中学教师的意见分岐严重。附中招生以后开学典礼时,我请院领导来参加一下,也一波三折,领导才到场。当时附中复校很困难,我去时领导答应给我七个讲师,但专业教员不肯来。起初,分配来的多是准备外调、让他们先在附中过渡一下的。文化课教员多数没有,像政治教员、英语教员、语文教员等等都没有,叫我去其他学校找兼职。学校一些部门也没有十分配合,反映给院里也迟迟得不到解决。负责具体分管附中的领导也不置可否,只说院务会议中我提出来:我这个三门教员(家门、校门、食堂门)书呆子干部,哪里来处理这种问题的能力?幸亏领导小组中的潘伦道和李宗杰同志有经验,故尚能维持维持。我以为要办就得办好,所以我就延迟开学,见口头汇报不行,后来就写报告,也无回音,我就直接找院党委书记。后来终于开学,并一代一代接下来,现在已成为著名的培养人才的基础学校。现在看了当时尘封已久的随记,原来办附中与否的事,1982年前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油画系有人是知道的,直到有人在喊:为啥党员不去?我说不要这样说,党员是有组织原则的,不去也得去。这样影响不好。
到附中碰到许多钉子后,院领导还提出要我们一个班子挂两块牌子,把大学部招收的师范班也放到附中来,我和老潘认为把大学生放在中专领导之下,如何说服这些学生?我和老潘坚决反对。
到附中两年后,我得了肝炎、肝肿,就提请辞职。有的领导说:再给你两个人,你只要动动口就可以了。自思不是这种料儿,就坚辞了。此后领导换届,新领导中的一位副院长,曾找我谈,叫我去掌管图书馆,我也谢绝了。
1985年底,发现自己患了直肠癌,幸好我爱人是个医生,处置及时,逃过一劫。此后变成纯粹的局外人。自思只要最上层领导正确,总会“自我完善”的,什么都会妥贴的。
离退休后,深感从来没有这么畅快地“我画我的”,而且可以随便使用较好的绘画材料。只要和平安定,像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将来会有好的陈列馆来陈列好的国画作品、油画作品及其他作品。学油画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困难。当然在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价值观也渗透到各个角落。一切向钱看的行为也花样百出。有的人早把昔日的誓言丢到不知哪里去了。改革开放以来,碰在枪口上的贪官也确实抓了不少,事实说明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好人也会变坏。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看来这种现象现在还相当普遍。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的确需加强。美术界的吹捧、造假,希望今后能少一点。油画“大师”有大师的规格不会很多。我们比起人家来,实在还少得可怜。
随便谈来,仅是度晚年的一种聊天的方式而已。有些像“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无济于事。
2006年3月